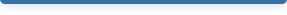张翼,社会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智库秘书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突出贡献专家,兼任中国社会学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等职务,曾挂职甘肃酒泉市委副书记。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国社会阶层流动、中国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就业与制度变迁等问题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新华文摘》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各级政府的研究项目。

1965年,张翼出生在甘肃省静宁县。从事社会学研究3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学术情怀,对学术孜孜以求,心无旁骛,潜心治学。在阶级阶层结构、城镇化、基层社会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等领域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张翼一直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理想,坚持把个人的学术志趣与国家、社会的需求相结合,不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9月20日,经提名、资格审查、学部评审、院外学术评鉴、公示、学部委员选举大会选举、院党组批准,我院产生9名新的学部委员,张翼位列其中。张翼目前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职务。10月11日,记者拜访张翼,借此深入了解他的学术成长之路。
“时代让我选择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老师您好!我是2019年7月第一次采访您,到今年正好认识您有5年时间。5年来,陆陆续续采访过您多次,对您也有一些了解。您本科时期其实并不是学社会学的,后来是什么原因或契机让您转向社会学研究的?
张翼:学人的道路选择离不开时代的影响。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先生约请费孝通先生重建社会学。在费先生的努力下,1979年成立中国社会学会,1980年1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费先生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努力下,社会学一时成为显学,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学子的关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体制改革如火如荼。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社队企业”为基础,拉开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序幕。费孝通先生写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回答了时代之问,掀起了学人对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热潮。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深受当时社会学各种著述的影响,并对这一学科产生了强烈的爱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事社会学研究数十年来,您一直践行着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孜孜不倦地耕耘着学术的沃土,并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在应用社会学方面。请您谈谈,您是如何保持对社会学研究的热情的?
张翼:我们这代人是最幸运的一代。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并在改革开放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改革开放注入的发展活力与动力,推进了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我国经过40多年的发展,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之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一动态变化的过程,使社会学人不仅能够观察社会的变迁,而且能够亲身参与和体验社会的变迁。一个学人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一旦与生动活泼的实践相结合,就易于将理论知识用于现实问题的研究,这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特点。作为社会学研究者,你更易于发现问题,但难的是如何学理化地分析问题,更难的是实事求是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些挑战本身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激励与研究热情。
同时,科研环境很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世界最大的社会科学院,也是世界最强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之一。我因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知识的海洋里泛舟,也因为经常能够见到那些曾经只能在图书馆才能见到的作者本尊,而被赋予了很强的荣誉感和崇高感。老先生们那种站在时代前沿的学术敏感性,以及他们经过学术滋养而形成的科研范式,经常激励我在懈怠时努力前行。有人带路、有世界上最富有洞见的人的指点,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他们的言传身教、他们的笔耕不辍、他们的著作等身,甚至他们把你作为团体成员的那种无私的批评,都能够激励你产生理论建构的想法。所以,实践是出题人,先生是引路人,我搭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便车,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力图从此岸到彼岸的那种学术冲动。
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既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也通过结构本身反射影响社会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重大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某些重大项目研究的机遇,也将我带入对社会流动、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问题研究的轨道中。我国汹涌澎湃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为社会结构变迁创造出了社会流动意义的“结构性机会”。为此,我写了《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一文。我想说明的是:一个人的努力是重要的,家庭支持也是重要的,但整个社会提供的“结构性机会”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代际之间的阶级继承,还是自己一生的流动,都深受整个社会变迁的影响。如果社会变迁创造的流动机会少,就只有少数个体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但如果社会结构变迁创造的流动机会波浪式增加,则整个一代人都会通过向上流动而改变自己的阶层地位。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社会动力,就使绝大多数农民子弟转变为“非农民”,而现在的农民不管是劳作方式还是生活水平,也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民不可同日而语。
学术研究与时代发展同频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有没有哪件事让您印象最深刻?为什么?
张翼:有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那篇《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原因与对策》文章,曾经引起过很大反响,带动过广泛讨论。当时有人评论说:不存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事实失衡,之所以在统计数字中出现女婴少于男婴的问题,只不过是没有统计到女婴——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第一胎生了女孩的家庭,不敢在人口普查中填报,从而造成了统计数据的“失真”。如果将漏报或隐匿的女婴填报出来,则不会发生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但我在现实调研中既发现存在女婴的“漏报”问题,也发现存在通过“胎儿性别鉴定”发生的流产手术问题——希望生男孩的夫妇会通过B超检查、并在确定为女婴后选择流产——由此导致男婴多于女婴的问题。虽然文章发表之初争议较大,但在学界多年的研究中,逐渐接受了我的学术发现。这篇文章也成为人口出生性别比研究领域比较早的一篇较为成熟的学术性文章。聚焦这一问题的研究,追踪其源头,大多会引用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高引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经有关部门简写上报,也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性批示。这篇文章的研究经历,让我深化了这样一个认识:如果你坚信自己的理论假设,如果你能够以翔实的数据做出论证,你就可以坚守自己的学术观点。学人的研究如果能够为国家所用,转化为社会政策,或者改革原有的政策,那是最大的成功。
二是关于当代中国中产阶层问题的讨论。2008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一文。这篇文章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写——大约有两年多时间,因为阶层问题非常复杂。当时,大多数学人认为中产阶层的扩大有利于社会的长久稳定。通常的说法是“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但考察东亚社会的中产化过程,或者考察拉美社会的中产化过程,甚至于考察西方国家的中产化过程,或者研究西方国家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们的政治态度及其行为,都会发现其作为“阶层”的表现与教科书意义的“稳定器假设”存在张力。由此,我费了很大周折来写这篇文章,断断续续研究,多次修改其中的表述,有时候连做梦都在思考这个话题,梦醒之后赶快写下梦里的想法。我的基本看法是,现代化一定会推进社会的中产化。但社会的中产化并不一定会一劳永逸地告别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大争论,也有人专门写文章与我商榷。后来,我还专门编了一本书,把我的文章和商榷的文章,以及其他论及此类议题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希望深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达及社会的本相。只有共同研究,才能通过“盲人摸象”的方式,从部分入手勾画整体。
三是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选择问题。以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推进城镇化战略?还是以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推进城镇化战略?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存在比较大的争论。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则蕴含不同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含义。国家的决策,只有与社会发展的进度、与人民的行动选择密切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因为对这一问题存有学术执念,我在参加国家计生委大型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时,就在其中设计了相关问题——实际也是几组操作性“变量”。成文之后,我在《中国人口科学》发表了《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一文。在研究中我发现,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的确希望通过“转户口”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但到新世纪之初,或者在现代化推进到一定程度,在土地的心理价值和宅基地的心理预期价值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农民工可能愿意到城市务工经商,但却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除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中心区外)。我的这篇文章对单纯用转变户籍以推进城镇化的制度配置进行了学术批评,主张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同城同权同待遇,在保护农民工在农村的基本权益的前提下,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我的文章给出的“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转户口”的这个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术圈和政府部门认定的“农民工都想转户口”的想法。到目前为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存在将近20%的差距。未来,伴随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伴随小农经济的终结,在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口流动的主流,将是从镇向县城,从县城向更大城市,从中小城市向地方性中心城市的流动。只有以常住人口配置基本公共服务,才能解决从定居化社会向迁居化社会的转型难题。还户籍以人口信息登记功能,解决流动人口在常住地的同城同权问题,这应该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科研之余,您还会时常练习写毛笔字。您觉得,写毛笔字和做科研之间有什么关系?
张翼:我写毛笔字是兴趣,不是练书法。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让眼睛离开电脑屏幕而休息,是一种室内分散注意力的做法。要说写毛笔字和做科研之间有什么关系,我还真有点感悟。写毛笔字本身存在一个写什么字体、随什么流派的问题。做学问也一样,也存在学派问题。现在学术研究的缺点,是没有学派,或者没有形成学派。很多人经常自嘲说自己是“自成一派”。这是典型的碎片化,很难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不赞成以西方的学术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做法,但要研究西方的学术流派,研究他们的团队建设,研究他们的话语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明确提出要建立自己的学派。在新一届党组的领导下,我们更好地掌握了科研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为我们建构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实践基础,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建构起自己的学派。我们只有充分解决了“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问题,才能形成梯队跟进、代际传承的良好局面。在这方面,我认为师承关系很重要。西方学派在其形成过程中——像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哈佛学派等,都存在师承关系。学派的建构本身就是有组织科研的重要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您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这是对您过去多年工作的肯定与鼓励。您觉得,您在哪些方面推进了应用性创新?请您选取一两个案例介绍一下背后的故事。
张翼:“全国创新争先奖”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后国家批准设立的重要科技奖项。绝大多数获奖者是科学研究人员,鲜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获此殊荣。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位获此奖项的科研人员,非常荣幸!如果不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估计我没有机会获得这一奖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申报此项奖项,必须在应用推广方面做出成绩。
我可以用两件事情作一个简要介绍。其一是论证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国家机关事务的运行保障问题,希冀以国家机关事务运行保障的现代化代替原有的机关后勤服务工作。我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机关事务运行保障研究中心”的建设,与其他学人联合推进了“政府运行保障管理”的学科化进程,使这一学科成为教育部学科体系中管理学门下一级学科——公共管理的二级学科。在我们团队的努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已经招收这一学科的MPA学员。
其二是推进了志愿服务研究。传统志愿服务经常以大型赛事化、名人效应化、节日化、大学生化等方式推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核心的志愿服务得到历史性大发展。我所做的工作,就是积极倡导将传统志愿服务转化为现代志愿服务,以志愿服务的体系化、专业化、治理化、社区化为抓手,建构人人需要志愿服务、人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大格局,将属于“文化”的志愿服务转变为属于“社会”的志愿服务,并使之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补充了人口老龄化和社区居民陌生人化所导致的社会服务供给力量缺口。我国社会的中产化过程,必然伴随志愿服务质量的提升过程。只有把志愿服务真真切切地与社区需求相结合,才能有针对性地把专业化的志愿服务传导到社区基层治理之中。我和我的团队通过调查研究,努力将理论社会学转变为实践社会学、将课堂教学转变为社会行动,产生了较为良好的影响。我们还申请创办了《中国志愿服务研究》杂志,成为全国第一本研究志愿服务的学术类期刊。
我想说的是,学人的研究,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才能产生应用性影响。幸运的是,我所做的工作,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使学术研究本身就可以直接服务于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工作。
要做坚守初心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家乡甘肃省静宁县及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对您当选学部委员高度关注。当地领导代表县委、县政府向您成功当选致以热烈祝贺并走访看望了您的家人。与此同时,您家乡不少父老乡亲在社交媒体上也纷纷留言说“祝贺”“静宁的骄傲”“静宁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为老百姓发声”……其实,从这些祝福背后,我们也能感受到,您家乡及家乡的父老乡亲对您的深深期许。对此,您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张翼:对于家乡父老乡亲的关注、对于静宁县县委书记何鹏峰和县长王蕾同志的关怀,我发自内心地表示感谢!我感恩家乡的养育,感恩下沟小学的培养。每当想起距离县城30多里的威戎乡的威戎中学,就会想起我的班主任王子郭老师!
小时候,我在放羊时,经常坐在一座山头,一边看书,一边畅想未来。但无论如何做梦,都没有梦想到我能够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的成长,离不开家乡这片热土的培育。静宁县虽然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但祖祖辈辈尊师重教、崇智尚学。每一任静宁县领导都遵从这些习俗,关心教育事业,引领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念本科时,当地的团委书记柴平武和副书记李旺军还特地赠送了40元路费——那时是一笔不小的支持,我一直心怀感激。
静宁县的乡亲对我评上学部委员的感受,与江南水乡名家众多人才辈出的地区的乡亲的感受肯定不一样。不管是县委领导,还是亲朋好友,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他们感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选拔制度的公平公正。他们说在一个祖祖辈辈务农的人家,在一个连乡长都没有出过的小村落,居然能够出一位学部委员,那是赶上了好时代!他们以我当选的事例教育静宁县的学生说:寒门学子可以靠勤奋努力实现中国梦!
我想对家乡的年轻学子说:“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在通往鲜花和掌声的道路上,必定会遇到各种坎坷、荆棘、迷惑,甚至是诱惑。但只有坚守初心的人,才能在学海无涯中找到那艘渡你到彼岸的大船。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采访您之前,我也随机采访了几位您的同事,他们用“智慧”“儒雅随和”“有趣”等关键词来形容您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印象。对于这些关键词,您是否认同?如果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自己,您会用什么呢?
张翼:听你这么说,我其实感触也很深。我认为,随和、亲和、谦和是我们社科院所有老师的共同特点,也是社科院这个学术机构的一种良好传承。
从读博士学位开始,我就从老师们的身上感受到了社科院的温暖。我的导师李培林,学富五车、为人谦和,对我的学问和人生总能及时给予指导。我在工作后与陆学艺老师同住在干面胡同的家属院,他给费孝通老师拜年,经常邀我一并前往。费先生胖大的身体自带智慧与随和,告别时总能给我准备一大包巧克力和进口香蕉。我有次获得某项科研奖励,雷洁琼先生亲自颁奖并留饭进餐,言谈中全是满满的慈祥。社会学人的华松品格、道德文章,无形中塑造了我的学术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家庭,对我的关心和爱护,让我受益良多。现在我也白发皓首,需要我将这些优良品质传承下来。
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但年轻的研究人员面临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也是很大的。科研工作需要代际之间的互相关心与密切合作。我希望我们能够塑造出一个健康向上、其乐融融的好环境,让大家都能够高高兴兴做学问,像朋友那样齐心合力读书写字。
如果要让我用一两个关键词形容自己,第一是勤奋,第二是感恩。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过程,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定环境。在国家蓬勃发展的重大时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把自己的学术人生融入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我深刻认识到,只有将学术研究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与社会需要相结合,才能使理论研究永葆学术青春。我们不是历史的过客,我们是历史的参与者。
在新使命下继续锐意进取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杰出代表。对于这一新身份,您是如何看待的?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在哲学社会科学界享有非常崇高的荣誉。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1954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实行学部委员制度。中国科学院在1955年选出了233位学部委员,后来又有所增补。1977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11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仍然使用学部委员制。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学部委员,随后定期选举。
所以,能够经过层层遴选并受聘担任学部委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最大梦想。我在表态发言中说,作为农家子弟,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就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能够当选为学部委员,实际是梦想之外多得的梦想。
我时常感慨自己的幸运。我有幸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盛世,有幸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座充满浓郁学术氛围的殿堂,有幸师从李培林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并长期在他指导下做研究,有幸在新一届党组领导下增选为学部委员。当选之前更多的是渴望,当选之后既感觉荣耀,又更感到沉甸甸的责任。未来,我将积极履行学部委员职责,坚守庄严承诺,为构建开放、包容、合作的科研环境不懈努力。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严谨的态度,投入到新的科研工作中去,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新当选的学部委员,您也将承担更多学术与咨询的责任,对于未来您有何规划?您该如何发挥学科带头人作用,推动并引领我国哲学社会学科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张翼:对于下一步的工作,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规划。第一,立足本职本责,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这是首要任务。第二,立足学科发展,发挥学科带头人作用,建设好团队,培养一批学术新人,增强学科学术影响力,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色的知识体系,彰显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特点。第三,做一个长远规划,希望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体会与思考,进一步知识化、专业化、学科化、系统化。如果每两年能够写一本书,那么,在70岁还能够完成5—6本书。这不仅是我对自己人生的承诺,更是不负学部委员光荣称号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