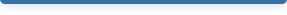楔形符号,主要流传于古代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从楔形文字入手,并逐渐演变为对古代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文化、历史和文明系统研究的亚述学,是中国学者深入理解古代世界文明的一把钥匙,对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坚定我国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专门设立亚述学研究中心,亚述学研究也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亚述学的当前研究进展如何?下一步有哪些研究计划?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亚述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洪更。
从楔形文字到古代文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亚述学是如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刘健:首先需要说明,亚述学(Assyriology)的命名源自今伊拉克北部的古代地名亚述(Assyria)。而今伊拉克南部的古代名称巴比伦尼亚(Babylonian),则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古巴比伦文明的源头。因此,亚述学和古巴比伦文明研究的地理、时间范围和主要内容其实是一致的。
亚述学学科建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一些西方探险者出于寻求基督教和犹太教源头、获取东方珍稀资源和个人猎奇等不同目的,前往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平原、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等地开展探险活动。这些早期探险活动最初主要是个人行为,之后丹麦、英国、法国等国的一些民间或官方组织开始资助这类活动,再之后英国政府支持的东印度公司则把持了这些区域的早期考古活动。早期探险者和考古人员陆续在这里发现了一些重要遗址,一大批珍贵文物资料和刻有楔形符号的泥板等被运送到英国、法国。这些资料为亚述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对楔形符号的研究在19世纪50年代初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851年,英国人亨利·罗林森成功破译了位于伊朗波斯波利斯郊外贝希斯敦岩壁上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铭文。1857年,在大英博物馆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来自英国、法国、爱尔兰的三位楔形文字研究者分别对这篇楔形文字进行翻译,得出大致相同的译文,这个活动可以视作一次楔形文字破译的成果验收会,标志着楔形文字解读的方向、方法是正确的。亚述学的学科基础就此奠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单一的楔形文字研究开始,亚述学是怎样逐渐演变为对古代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文化、历史和文明的系统研究的?
国洪更:公元1世纪左右,在域外民族征服和同化的过程中,两河流域文明的光彩日趋暗淡。不过,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模糊地残存在犹太人的《旧约圣经》和希腊罗马史家的作品中,吸引中世纪欧洲旅行家去探索。随着英法两国考古学家在亚述故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大量带有楔形符号的文物重见天日,极大地推动了亚述语楔形符号的释读。19世纪晚期,英法两国再掀西亚考古高潮,德国、荷兰、丹麦、捷克和美国等欧美国家相继加入,带楔形符号的大量文物涌入欧美国家和私人博物馆。随着楔形符号文献的编辑出版,欧美国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亚述学研究蓬勃发展,尘封2000多年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随着学界对赫梯语、埃兰语、埃布拉语、乌伽里特语和乌拉尔图语等两河流域周边地区语言的楔形符号释读不断增加,西亚地区的上古文明多样性随之凸显,学界对两河流域文明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的认识逐渐清晰,在此背景下,亚述学逐渐从单一的楔形符号研究演变成对古代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和其他学科相比,亚述学在研究视角或方法上有哪些独特之处?
刘健:亚述学是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平原及其周边文明的学科。它以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运用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方法开展研究的一个综合性学科。在19世纪50年代,主要依据出土文献开展学科研究是亚述学研究的突出特色,更早兴起的埃及学与亚述学相同。与当时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古典学相比,这两个学科并无传世文献作为研究资料依托。另一方面,考古发掘在亚述学学科体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亚述学最突出的学科底色就是考古学与语言学、文献学研究并重。
从学科话语上来看,亚述学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它的“西学”特征。这是一门主要由西方人构建的学科,早期的科研和教学机构主要集中在西方各国,至今亚述学研究的中心仍然在美、德等西方国家。因此,亚述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西方话语特征。举例而言,1872年12月3日,在楔形文字研究历程中发生过一件颇有影响力的事件。这一天,大英博物馆主办圣经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会上,大英博物馆馆员乔治·史密斯作题为“迦勒底人的洪水故事”的发言,报告他在解读考古学家奥斯坦·莱亚德和霍尔木兹德·拉萨姆在尼尼微阿舒尔巴尼拔二世王宫发掘中出土的部分泥板的成果,宣布他发现了《旧约圣经》中著名的洪水故事,引起与会人员、大英博物馆以及部分英国政府官员的高度重视。1873年1月,乔治·史密斯就带着大英博物馆筹集的资金出发前往尼尼微开展楔形文字文献发掘工作,并很快取得重要发现。此后,楔形文字泥板成为亚述学考古发掘的主要目标,改变了此前以发掘大型纪念性建筑和“珍宝”为主的发掘目标。这次的发现对亚述学研究主题的选择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乔治·史密斯指出,他发现了传说中人类最早的家园,是伊甸园的所在;发现了比大洪水时期还早的城市;发现了宗教的发源地。这里的艺术和科学是希腊人的,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即大多围绕西方学界的传统话题,尤其集中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与《旧约圣经》传统的关系、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源头、在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建立文化纽带。
美国学者塞缪尔·克雷默是研究苏美尔文学和文明起源的著名学者,他追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时,从政府和政治、教育和文学、哲学和道德观、法律和公正观等角度进行总结,西方话语味道十足。这同样也是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出发点,不少学者在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遗产时,都将主要目标放在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上,正如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哈罗所言,他对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制度的研究目标是“展现古代近东人的发明创造和思想观念如何留存至今……在何种程度上现代西方仍然受益于古代近东”。
国洪更:从研究对象上来看,亚述学是一门研究那些使用过楔形符号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早期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亚述故地,发掘的楔形符号被称为亚述语,这门科学因此被称为亚述学。不过,细究起来,“亚述学”一词并不准确,因为亚述语只是众多使用楔形符号书写的语言之一,亚述也不过是众多使用楔形符号的西亚古国之一。因此,现在也有学者建议将亚述学改称为“楔形符号研究”“楔形文字研究”或“古代近东研究”。
目前,随着西亚地区考古发掘范围的扩大和楔形符号文献研究的深入,亚述学研究早已超越了亚述地区文明存续的时空范畴。从时间上看,亚述学主要研究从公元前3200年楔形符号的诞生到公元1世纪楔形符号被弃用之间3000多年的时段,有时溯及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后延至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从空间上看,亚述学主要关注今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南部和东南部以及伊朗西部地区,但时常囊括黎巴嫩、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埃及北部和亚美尼亚等影响和接触过的区域。从研究对象看,亚述学研究涉及古代西亚地区文明的全部,包括语言、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宗教、建筑、艺术、科技以及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从这个意义而言,它并非一门单独的学科,更像一个与楔形符号研究相关且互相援引的学科集合。
楔形符号是古代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使用了3000余年的主流书写符号,并在自然演化中成为上述区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楔形符号文献也由此成为西亚地区文化的重要载体,文献学的研究范式是亚述学家最为倚重的研究方法。此外,亚述学与考古学水乳交融,很多亚述学家积极参加考古发掘,亚述学家解读楔形符号文献需要借助考古学的成果和手段。出土文物不仅具有历时性特征,而且烙上了民族的印痕,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时常被亚述学家借鉴。楔形符号书写的语言种类各异,时常互相融合,亚述学家释读楔形符号文献经常借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入选冷门绝学具有强烈现实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亚述学在国内的发展现状如何?
国洪更:从16世纪80年代起,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介绍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知识。晚清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主动介绍亚述学知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部分高校也开始讲授古代两河流域史。但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中国真正的亚述学研究始于1984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创建。根据“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一批外国亚述学家被延揽至中国进行亚述学教学,一批优秀的亚述学学生赴欧美著名亚述学研究机构深造。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亚述学人才的成长和海外留学人员的回归,中国的亚述学初具规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十余家单位已开展亚述学教学与研究,其中亚述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已达6个。中国亚述学学者可以熟练使用赫梯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等古代语言以及英语、德语和法语等现代语言,系统地研究古代西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多项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出版论著也受到多层面的奖励,并与荷兰、意大利、德国、法国、比利时、芬兰、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等国亚述学研究实力雄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学术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亚述学研究中,我院主要聚焦哪些研究分支和研究领域?
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将亚述学纳入学科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亚述学及分支学科赫梯学研究领域,先后引进4名研究人员,目前,所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只有我和国洪更两位研究人员。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在开展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等级制度、民族与宗教起源、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等若干重大理论和学术问题的集体研究时,都将相关亚述学和赫梯学专题纳入其中。此外,上述学者在古代社会演进、文明起源、官僚制度等专题上产出了一系列成果。围绕上述主题的专著、论文在国内学界获得较好评价,多数成果获得院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多篇论文获转载。其中,杨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2023年更名为古代文化(西亚北非)研究所),曾参与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课题研究。易建平是院长城学者,他对赫梯王权的研究论文曾获得胡绳学术奖。我和国洪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这也是国内最早开展亚述学教学的机构。我主要从事亚述学和赫梯学研究,参与等级制度、民族与宗教起源、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等集体课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担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秘书长等学术职务;国洪更主要从事亚述帝国史研究,他的著作《亚述赋役制度考略》曾获得第十届(2019)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较于国内其他高校机构的亚述学研究,我院在亚述学研究中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院对此有哪些扶持和帮助?
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述学学科能够覆盖亚述学研究的主要时段,研究集中在诸如文明起源、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思想等重要主题,在国内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同时,作为“国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这两个研究机构以及新成立的亚述学研究中心为中国亚述学研究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在人才培养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21世纪初开始招收亚述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生,专业方向一般表述为古代西亚史、古代两河流域史;在2024年招生目录中进一步明确为亚述学。我们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虽然面临一些困难,但保证了学脉传承不绝。至今已培养硕士研究生6名,目前在读博士研究生3名、硕士研究生1名、在站博士后1名。多数硕士毕业生在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其中1人现任教于北京大学。自2018年开展本科生教学以来,我们还在多门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中纳入亚述学专题,对古代西亚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围绕文明和国家起源、古代国际关系、王权、亚述学学科构建等问题进行专题讲解,以此拓展亚述学的公众互动,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亚述学为何会被列入冷门绝学?
国洪更:亚述学重点关注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最早的原生文明之一。汗牛充栋的楔形符号文献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为系统地考察古代文明产生、发展及其衰亡的历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亚述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古代世界文明的认识。西方文明脱胎于基督教文明,后者根源于希伯来文明和希腊—希腊化文明,而这两种文明的源头都可以追溯至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因此,亚述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探寻西方文明的最终源头。
楔形符号书写体系极其复杂,同形不同音、同音不同形颇为常见,区区5个楔形符号的组合变化数以百计,掌握楔形符号耗费的精力难以想象。除古波斯语等少数语言外,楔形符号书写的语言多已死亡达2000多年之久,留下的未解之谜不计其数,且不说迄今为止语族归属尚未确定的苏美尔语。黏土是楔形符号的主要书写材料,埋藏2000多年的泥板出土时往往碎成多块,早期掠夺式考古发掘增加了恢复原状的难度,识别、拼接破碎的泥板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有时甚至仰赖于运气。因此,虽然亚述学诞生已超过150年,释读的楔形符号文献也数以万计,但是,据不完全统计,已出土带楔形符号的文物多达50余万件,楔形符号文献多达1300万个词。和如此海量的研究文献相比,过往的研究不过仅仅触碰了冰山一角,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胜枚举,非专业人员往往望而却步,仅有少数亚述学家踽踽而行。亚述学是一门名副其实的冷门学科,某种意义上更需要通过一些特定的政策倾斜和帮助延续、发扬学科。
此外,虽然中国亚述学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一是研究人员较为分散,一个单位往往仅有一名亚述学学者,无法开全亚述学必修的专业课程,难以培养合格的后备人才;二是中国亚述学学者往往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难以齐心合力谋划未来的发展;三是中国亚述学选题较为分散,重大选题的集体项目少之又少,难以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推动中国亚述学的良性发展,中国亚述学学者需要集思广益,形成合力,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创建资源共享的研究平台,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统筹全国的研究力量,策划国家急需、学科倚重和公众关心的重大选题,推出更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为亚述学研究搭建新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亚述学领域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刘健:从国际亚述学研究来看,对考古发掘、文本研究、文献整理的微观研究和整理工作越来越广泛、深入,但是综合性研究相对较少,对文明、历史的中观和宏观研究也较为不足。最大的问题在于,亚述学的“西学”特征十分明显,主要科研和教学机构集中在西方国家,研究者也大多为西方学者,在研究主题选择上具有鲜明的“西方”色彩。西亚各国本土学者十分稀少,没有形成有力话语权。
国洪更:亚述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学科的边缘化,它并非来自外部影响,而是源于亚述学家自身。亚述学诞生于兰克学派鼎盛的时代,也深深地打上了其烙印。数量远超其他古代文明的楔形符号文本文献是亚述学研究无与伦比的优势,但许多亚述学家过分拘泥于编辑整理楔形符号文献,不仅难以跟上学术发展的潮流,而且逐渐远离了公众视野,这对学科的发展并无益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亚述学未来的研究方向有哪些?
刘健:亚述学未来的研究首先应坚持传统学科特色,从文本入手,从考古资料和图像资料等原始资料入手,探索文明的精神特质、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提炼具有共同文明含义的标识性符号,研究文明的根本特性及其对世界、自然、社会的理解。其次,开展文明比较研究,提炼共同的文明标识符号,增进文明间的对话,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提供学理支撑。
国洪更:目前已释读的楔形符号文献仅占少数,诸多领域依旧存在空白,但是,亚述学家的贡献不容置疑,古代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文明的发展脉络已基本厘清,突破文献学研究范式的桎梏,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从整体上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文明不仅可行,而且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的亚述学研究起步晚,可以充分吸取国外同行的经验教训,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中国亚述学学者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梳理古代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文明发展历程,深入剖析文明形成阶段、鼎盛时期、黑暗时代与没落阶段的基本特征及其原因,总结古代西亚居民取得成功的经验、应对挑战的策略和最终灭亡的教训,汲取他们的智慧和力量,为破解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国家队”,我院在亚述学研究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刘健:目前,中国的亚述学学科仍然面临研究人员极度短缺、研究领域有限、国际影响力不足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在亚述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研究和教学系统化规范化上下功夫,团结和组织国内学者围绕文明起源和发展、文明特性研究等具有重要比较意义的主题开展集体研究,加强基础资料建设,积极组织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亚述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亚述学发展带来哪些机遇?
国洪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包括亚述学在内的冷门绝学学科出台的新扶持和帮助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设立专门的冷门绝学学科,每年予以资助,计划连续资助5年;二是在研究生招生计划中予以倾斜,为亚述学等冷门绝学提供专门的招生名额。与此同时,立足院所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也将对包括亚述学在内的冷门绝学予以帮扶,在权威刊物《世界历史》开设冷门绝学栏目,专门刊发亚述学等冷门绝学学科的学术论文,为学者提供交流平台。
刘健: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的成立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高规格的平台,为构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极大助力。依托这个新平台,亚述学研究中心将有机会扩大招生规模、拓展国内外交流渠道、团结国内外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冷门绝学研究是基础学科,具有从业人员少、研究难度大、培养周期长等特点,协同创新机制将为团结各领域研究者提供新契机,有助于克服目前面临的困境。首先,在人才培养机制上有望形成合力,在语言文字、基础文献训练上联合其他高校开展团队教学,为学生提供相互交流促进的平台。其次,在学科建设上,有助于获得开展基础建设的机会,包括集体开展资料建设、基础名词整理、基本主题设定等,形成团队优势。最后,从文明研究的角度,不同学科之间的协同研究有助于建设和传播文明研究领域的中国话语体系,有利于中国学者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