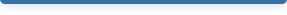和卫国(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方志是介于宏观国史、微观家谱之间最具中国本土特质的中观历史文献载体。千百年来,方志编修以国家治理、社会建构和文化生成为内生动力,特别是明清以来国家“大一统”观念不断强化,推动形成了赓续不断的时间脉络和“天下郡县莫不有志”的空间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此肥沃的文化土壤中,方志学应运而生。
“方志学”立名
方志成“学”与宋代方志定型不无关系。北宋元丰年间,太常博士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开篇即有“方志之学,先儒所重”之语,其义当指方志编修这门“学问”,后世沿袭“方志之学”的表述较多。
1921年印行的《宿松县志》卷32《艺文志》总叙有言:“方志,以上备国史甄采者也。为方志学者,谓为国史之具体而微,媲于晋《乘》、鲁《春秋》、楚《梼杌》及《国语》、《左传》、十二国宝书之类(清乾隆间会稽章学诚力主此说),其言甚辨,具根史法,虽不尽然,弗远于中焉。”已明确使用“方志学”一词,并对清代史家章学诚所论史、志关系给予肯定。惜其为志书叙文,未能展开论述,也未引起社会关注。
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第21卷18号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后收入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篇专论方志学内涵及清代修志成就,堪称经典。其核心之论有:“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因梁启超声望较高,在其倡导下,章学诚被奉为方志学鼻祖,“方志学”作为专有名词开始被广泛使用,甚至梁文还被一部分人视为方志学学科产生的标志。
梁启超方志学概念解析
梁文高屋建瓴,影响至深,毋庸置疑。但是,所论三个核心问题仍需辨明廓清。
其一,梁文所谓方志学,是以乾嘉学派为中坚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的一部分,也即清代方志学,仍属于传统意义上方志编修的学问。这是梁文立论之基。
其二,梁文全篇对章学诚推崇备至,将其定位于方志学的创立者,依据在于“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众所周知,宋代以后方志体裁体例不断丰富,但直到清代四库馆臣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将其归入史部地理类。在梁启超看来,方志之所以成“学”,是因为章学诚从学理层面彻底改变了自古以来将方志视为地理书的观念,强调修志应遵循史家法度,并提出了方志分立志、掌故和文征“三书”,设立志科等修志方法,“概念扩大,内容自随而扩大”,“内容组织亦随之而异”。这是梁文所论方志学的核心。也正因从学理和方法两方面“重新发现”章学诚,方志学在梁文中才成为了不仅与史学、地理学并列,还与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历算学、金石学等相提并论的专门学问。
其三,尽管梁启超批评很多清代方志“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但又以其提倡的“新史学”重塑了方志的文献价值,认为以往史家“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方志则正可补史文之缺,“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在章学诚方志思想基础上,对方志本体的认知得以深化,也开创了未来方志服务社会史、区域史研究的先河。
方志学百年变迁概观
民国时期,社会风云激荡,然而方志编修从未中辍,志书在门类设计、内容记述等方面也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和现代知识体系划分的特征,方志学研究对此作出了回应。
新中国成立后,方志编修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引领和支撑下重新启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完成两轮大规模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为方志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以往方志学探讨的各个主题,作为相对独立的分支被置于现代方志学学科体系之中。回溯方志学百年演进历程,可以概括出三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一是实现指导思想由资产阶级史观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转变。身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方志学的“偏见”,还揭示出方志记述各地社会发展变化的特殊价值,正契合其倡导“史界革命”批判帝王将相历史,书写社会、民众历史的需要。民国时期方志编修和方志学研究深受此影响。
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基本观点,思想极大解放,记述内容更加丰富。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书写中国历史发展演进,也因此成为现代方志学研究的主线。
二是实现方志学由融入新知识的传统学问向现代学科转变。民国时期,在服膺章学诚方志思想基础上,受近代社会变革影响,方志学研究范围扩大,涉及方志历史、框架设计、体例体裁、内容记述等,一些论述不乏开创意义,对方志学体系形成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受修志实践、人才队伍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论述依据资料有限,探讨编修具体问题为多,内容亦显简略,整体上仍未超出传统学问范畴。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两轮大规模修志生动实践,为方志学研究内涵和外延的拓展提供丰厚滋养,也提出了更高理论要求,从而形成方志学史、方志学理论、方志编纂学、方志文献学、方志目录学、方志数字人文、旧志整理等多个研究方向,知识体系得到系统梳理与建构,学术性、理论性极大增强,初步建立起兼具编修实践、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三重特征的现代学科体系。在此背景下,2022年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合作,在全国率先设置方志学二级学科,培养方志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展专业研究。
三是实现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由零散化、基础化向组织化、专业化转变。清代及其以前,方志学观点主要借助志书序跋、凡例或个人文章得以阐释。民国时期,政界、学术界众多人士参与修志,产生了一批修志名家和方志学著述,如李泰棻《方志学》、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王葆心《方志学发微》、甘鹏云《方志商》、黎锦熙《方志今议》、寿鹏飞《方志通义》等,此外《禹贡》《东方杂志》《国学丛编》《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方志编修专文,方志目录则以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为代表,部分图书馆编制有馆藏方志目录。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普遍设立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专职组织修志,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和众多高校、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纷纷投入专业研究之中,涌现出大批研究方志的专门家和代表作,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方志学理论著作1000余部,发表论文10万余篇。其中,方志通论性质的著作有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黄苇等《方志学》、来新夏等《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方志学概论》、吕志毅《方志学史》等,此外还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方志通鉴》《方志百科全书》《中国地方志论文论著索引(1913—2007)》等众多大型工具书,成为方志学研究专业化、系统化的重要支撑。
方志学未来展望
方志学自产生以来就是一门建立在方志编修实践基础上的学问。展望新时代方志学发展,其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总结修志实践经验并上升到学术和理论高度,用以更好地指导未来方志编修实践,不断丰富完善方志学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推动中国方志文化发扬光大。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重写方志发展史为抓手,深度梳理方志发展基本轨迹、历史成就、时代特征,在准确把握方志发展规律基础上,对方志学学科远景作出前瞻性展望和规划。
二是深刻理解方志学肩负的时代使命,研究、推动志书体例体裁和内容记述的改革创新,探索如何更加客观、全面、系统、规范地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辉历程,在新时代文化舞台上充分展示方志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是强化独立学科意识,丰富学科内容,夯实学科根基,树立学科规范,努力构建具有典型本土特征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全面巩固中国方志文化的主体性特征。
四是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积极探讨方志学与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关系,深入探寻学科间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确立方志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地位,形塑交叉学科的基本范畴和发展逻辑。
五是秉持学以致用、修志为用双重理念,以学科、学术和时代三重眼光审视方志编修成果,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新方志和历代旧志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努力实现方志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六是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和研究梯队建设,打通理论研究与修志实践之间的障碍,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方志学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