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是指依托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并利用算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生产与市场交易的新兴企业形式。从数字平台企业数量与市场规模来看,目前我国平台企业的经济体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互联网平台企业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形成垄断的弊端。数字平台企业具有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零边际成本等优势,通常跨业务领域开展经营活动。多领域经营的超级数字平台企业很容易成为垄断市场的巨型企业,并出现恶性竞争与侵犯用户权益等现象。平台企业的发展对数字平台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数字平台的双重性
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正在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平台企业的崛起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全球现象。无论是境外的微软、苹果、亚马逊,还是我国的腾讯、阿里、美团等,均在快速扩大业务范围。随着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元素的加入,大型数字平台的服务辐射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数字平台业务扩展相伴随的是,数字平台的公共属性正逐步显露。王磊认为,公共设施应具备两个核心特征:第一,行业具有较高进入门槛,运营方缺乏竞争对手;第二,设施的运营业务为公众所必需,用户的经济行为与社会交往严重依赖该业务。从这两个标准来看,大型数字平台已经具备了公共设施的基本特质。首先,数字平台经营存在明显的网络效应,大数据模式对数据的收集分析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这对数字市场形成了非常高的进入门槛。其次,相较于运营方对用户的控制,用户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和依赖性。
在平台运营中,可以明显看到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所说的数据规律支配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以电子支付为例,由于免去了现金支付的烦琐,即刻到账省去了找兑等问题,微信、支付宝等方便快捷的电子支付形式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支付方式。数字平台企业还承担了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比如,水、电、气等基本公共服务也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轻松接入。大型数字平台通过对社会生活数字接入端的控制,可以轻易调控用户的社会行为。可见,数字平台已经可以被视为公共设施。
作为公共设施的数字平台具有双重属性,数字平台是私有性企业,同时又因业务的服务范围与业务性质而具有社会公共性。平台型企业如果能充分认识到平台的公共属性,不仅通过数字平台实现经济价值,而且能够推进社会价值,那么平台企业则可以通过行业自治的方式进行自我规范。然而,作为私营企业的数字平台仍然遵循资本逻辑追求营利,运营的终极目标仍然是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在数据成为盈利条件的同时,数字平台型企业倾向于用数据来获取经济利润。由此,数字平台型企业的经营与社会责任之间显现出巨大的张力,数字平台的公共性与企业的营利性之间形成了紧张关系。阿莱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认为,互联网时代的个人数据储存在私营企业数据库中,普通用户无法自由使用数据库,这严重妨碍了民众的知情权。私营机构收集的位置信息、交易记录、通信内容等数据,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变相剥夺。
数字平台反垄断
2021年是我国数字平台反垄断的开局之年。在此之前,欧美国家大多已启动针对平台企业的反垄断治理举措。2020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草案。2020年10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布《数字市场竞争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着重指出了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等平台企业在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各领域的垄断行为。为了回应业界与学界对数字平台反垄断的呼吁,2020年12月,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的要求。2021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2021年,国家多个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数据保护、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与政策。此后,我国互联网管理部门开展了互联网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平台经营者过度集中与数字平台“二选一”等问题。
在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中,反响最为强烈的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的“二选一”行为作出的处罚。阿里巴巴平台的“二选一”行为,损害了商户与消费者的利益,平台之间的竞争被抑制,严重背离了平台企业开放共享的经济理念。对阿里巴巴的处罚决定书指出,天猫、京东、拼多多等竞争性平台之间存在明显的规模不平衡。阿里巴巴的强制性“二选一”做法使处于不利地位的电商平台很难维持市场地位,甚至可能被迫退出市场。王晓晔认为,竞争者退出市场不是因为产品和服务本身,而是因为平台强制实施“二选一”减少了其用户的数量,这会造成一种扭曲的竞争。数字平台企业使用“二选一”等强制性措施,恶意排除竞争对手,或者阻止新的企业进入市场,从长远看也会损害平台市场的公平竞争。
当平台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为具有公共属性的数字平台时,就需要承担开放平台、数据互通等公共性义务。大型数字平台的对外开放,并不可能像公共机构那样面向全社会免费公开使用。如果平台治理以法律形式强制平台企业对所有竞争对手开放,将会导致“搭便车效应”,严重挫伤平台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的关键是要找到平衡的治理方式,既保护平台企业的创新性,又能够防止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妨碍公平竞争。
合作性治理框架
平台企业得益于规模效应,表现出极高的创新性,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率提高与数字经济增长。
数字平台企业之所以有较高的生产率,是因为平台的规模经济以低成本带来高产出。另外,数字平台的长尾效应也非常显著,一旦数字平台站稳脚跟,服务规模扩张的边际成本将接近于零。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服务的范围也随之扩展,所以,数字平台的规模经济具有普惠性的价值内涵。数字平台企业的经营不同于传统行业,所有的业务类型基本都以创新为基础,平台企业的创新产品又不断孵化出新的社会功能和相应的服务。数字平台的反垄断治理并不是要扼杀平台企业的创新热情与创造动力。合理的规制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合作性治理机制,为数字平台的协调发展保驾护航。
从平台反垄断治理的现状来看,目前各个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我国平台企业的监管部门既有人民银行、工信部等行业监管部门,又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监管部门。为了更好地监测评估平台企业的市场行为,应该考虑建立综合性的平台企业监管机构,以提高数据使用规范、用户权益保护与反垄断等政策的匹配性。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理论认为,平衡的治理要求政府创造理性、开放、常态化的对话体制,以便推进政策妥协和政策学习;既不抑制平台企业的创新性,又不纵容平台无限度扩张,妨碍公共利益;除了法律法规的规制与政府行政监管之外,还需要建构一种吸纳社会规制力量的合作性治理框架。
社会性规制力量主要来自社会监督与行业自律。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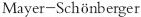 )等人提出了“算法师”的概念,并希望以其对算法的熟练掌握和公正的社会准则的坚持,对数字平台企业监管提供社会性支持。算法师不是技术性个体,而是一种以大数据为依托的专业技术机构,负责监测数据操作的透明度。维克托将算法师分为外部算法师和内部算法师。外部算法师相当于数据审计员,提供大数据审计与应用程序安全性监测等服务。政府和算法师可以就公共领域大数据的使用进行技术磋商,进而把社会性监督力量引入平台治理中。与外部算法师的社会公益性不同,内部算法师具有明显的行业自律属性。他们负责在平台企业内部监督数字平台的大数据活动,需要在行政与法律规制介入之前,对数据操作的合规性进行内部审查。将社会性规制力量引入平台治理的合作性框架,有助于形成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认知,长期来看可促进数字平台的社会性嵌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
)等人提出了“算法师”的概念,并希望以其对算法的熟练掌握和公正的社会准则的坚持,对数字平台企业监管提供社会性支持。算法师不是技术性个体,而是一种以大数据为依托的专业技术机构,负责监测数据操作的透明度。维克托将算法师分为外部算法师和内部算法师。外部算法师相当于数据审计员,提供大数据审计与应用程序安全性监测等服务。政府和算法师可以就公共领域大数据的使用进行技术磋商,进而把社会性监督力量引入平台治理中。与外部算法师的社会公益性不同,内部算法师具有明显的行业自律属性。他们负责在平台企业内部监督数字平台的大数据活动,需要在行政与法律规制介入之前,对数据操作的合规性进行内部审查。将社会性规制力量引入平台治理的合作性框架,有助于形成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认知,长期来看可促进数字平台的社会性嵌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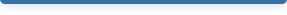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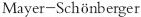 )等人提出了“算法师”的概念,并希望以其对算法的熟练掌握和公正的社会准则的坚持,对数字平台企业监管提供社会性支持。算法师不是技术性个体,而是一种以大数据为依托的专业技术机构,负责监测数据操作的透明度。维克托将算法师分为外部算法师和内部算法师。外部算法师相当于数据审计员,提供大数据审计与应用程序安全性监测等服务。政府和算法师可以就公共领域大数据的使用进行技术磋商,进而把社会性监督力量引入平台治理中。与外部算法师的社会公益性不同,内部算法师具有明显的行业自律属性。他们负责在平台企业内部监督数字平台的大数据活动,需要在行政与法律规制介入之前,对数据操作的合规性进行内部审查。将社会性规制力量引入平台治理的合作性框架,有助于形成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认知,长期来看可促进数字平台的社会性嵌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
)等人提出了“算法师”的概念,并希望以其对算法的熟练掌握和公正的社会准则的坚持,对数字平台企业监管提供社会性支持。算法师不是技术性个体,而是一种以大数据为依托的专业技术机构,负责监测数据操作的透明度。维克托将算法师分为外部算法师和内部算法师。外部算法师相当于数据审计员,提供大数据审计与应用程序安全性监测等服务。政府和算法师可以就公共领域大数据的使用进行技术磋商,进而把社会性监督力量引入平台治理中。与外部算法师的社会公益性不同,内部算法师具有明显的行业自律属性。他们负责在平台企业内部监督数字平台的大数据活动,需要在行政与法律规制介入之前,对数据操作的合规性进行内部审查。将社会性规制力量引入平台治理的合作性框架,有助于形成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认知,长期来看可促进数字平台的社会性嵌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