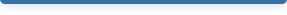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学经历了传统与现代、中学和西学的碰撞、融合。张荫麟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者,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其史学研究也受时代风潮影响。从他对历史的认识、研究历史的方法及其史学风格,可窥见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型和时代之思潮。
“统贯”历史发展范畴
历史观包括历史哲学、史料观和历史编撰法三个方面。就历史哲学言,张荫麟最重要的见解体现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和《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中。他的重要贡献有两方面:一是对传统历史哲学的“抉见祛弊”。张荫麟将传统历史哲学家探求的法则分为五类:历史的计划与目的、历史循环律、历史“辩证法”、历史演化律和文化变迁之因果律,并将其分别对应不同的历史哲学。他对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理想史观、唯物史观、气候史观和人物史观进行了辨析和阐释,特别是对将黑格尔视为目的史观的集大成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二是总结归纳了历史发展的范畴。他认为历史不仅是“一时的静的结构的描写”,而且是“变动的记录”。他将其归纳为因果和发展两大范畴,而发展的范畴包括“定向的”“演化的”和“矛盾的”三个小范畴。他也承认这四种范畴不能涵盖历史上全部的史实,在这些范畴之外的史实乃为历史上的偶然。对于偶然,他从历史本身和人类认知的角度将其分为“本体上”和“认识上”两种,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尽量减少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
提出“笔削”之标准
就史料观言,张荫麟的见解体现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中,提出了“笔削”的标准。所谓“笔削”也就是剪裁,即在历史书写中如何选择史事。史事本于史料,“笔削”的标准即选择史料的标准。笼统地说,“笔削”的标准在于史事的重要性过于含混不清,因此张荫麟提出了更具体的标准:新异性、实效、文化价值、训诲功用和现状渊源。
张荫麟也认识到了史料的局限性。他认为史料的限制有绝对、相对之分。绝对限制包括观察范围、观察者、观察地位、观察时之情形、知觉能力、记忆、记录工具、观察者之道德、证据数量、传讹、亡佚。相对限制包括由绝对限制而产生的谬误、伪书与伪器之未经发觉者、史家对史料的误读、事实之解释。对此,张荫麟列举的情形具体详备,但也有琐碎和交叉重复之弊。
对于史料的局限性,张荫麟试图减轻、克服。他认为随着科学和史学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者的增多和分工的精细将减轻相对限制。绝对限制也会因教育的发达、印刷术的流行、图书馆博物馆的兴盛而减轻。他特别看重报纸作为史料的巨大价值。此外,他颇有创见地提出了“历史访员制”,呼吁社会的同情与赞助,组织学术团体,依科学方法观察记录当下人类活动以保存现代史料。从这一角度看,张荫麟可以说是提倡“公众史学”的先锋。
贯通“专博”、追求“真美”、兼顾“雅俗”
张荫麟的历史编撰法不仅在学术专论中多有论述,也体现在其历史研究和通史编撰中。首先,他强调贯通“专”与“博”。博古通今本是史学的传统,但随着“西学东渐”的风潮,传统史学走向了专科化研究之路。张荫麟认为“观史”有钻观、纵观、横观三种方法。钻观、横观偏于“专”,而纵观偏于“博”。这对应不同的历史编撰思路,需针对不同目标读者采取不同编写思路,对专与博各有侧重。
其次,在历史编撰中张荫麟追求“真”与“美”的统一。他认为历史世界与自然世界一样,既是审美对象,也是穷理对象。作为审美对象的历史为“艺术化之史”;作为穷理对象的历史为“科学化之史”。两者的目的都是“显真”,前者所显为“真相”,后者所显为“真理”。这些论述体现了张荫麟论史的哲学思辨性和理论创建力。他推崇中国传统历史书写中的修辞用典,认为可提升历史之美。张荫麟历史写作的文笔修辞极具美感。
此外,张荫麟有意识地兼顾“雅”与“俗”。除了“真”与“美”,“致用”也是史学追求的价值。他写通史、编教材“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他认为历史写作的目标读者不仅是学界的专业人士,更包括社会民众、青年、孩童。因此,雅俗共赏、简明易懂、意趣盎然是张荫麟通史写作的目标,而实际上也成为其《中国史纲》《儿童中国史》的鲜明特色。这一点与当下“公众史学”的理念也不谋而合。
回归中国历史研究
张荫麟的历史研究始于考据,成名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是典型的考据文章,其后的《荀子解蔽篇·补释》《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等也是同类之作。但他并没有囿于考据之学,在清华大学读书和留学美国期间,他关注到中国科技史和西方史学,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中西交流史,翻译、引介西方史学理论,写就了《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张衡别传》《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历史之美学价值》和《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等。
张荫麟对西方哲学和社会学兴趣浓厚,在美国求学期间受到系统训练,《斯宾格勒之文化论》《道德哲学之根本问题》《道德哲学与道德标准》和《说可能性》是他社会学和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他认为实现史学转型要借助哲学革新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借助社会学认识历史上的社会构造和社会变迁。经过哲学和社会学的训练后,他选择回归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在宋史领域,以跨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了《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南宋末年的民生与财政》《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等作品。
“时风”与“学风”
通过对张荫麟历史观和治史路径的考察,可发现其史学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史学思潮之关联。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融合哲学和社会学之自觉。张荫麟对历史和历史理论进行哲学反思,并自觉运用哲学思维和社会学理论进行中国历史研究,以达到“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二是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之彰显。在战乱纷起的动荡时代,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国人心头,张荫麟也不例外。除了《中国史纲》《儿童中国史》,从《上海英日人八次惨杀我国同胞始末》《智识阶级应当怎样救国?》《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等文中,可以鲜明地看到他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
三是空间与时间之“增减”。“空间之增”指历史研究的空间扩大,除中原地区外,关注边疆、世界,把眼光从帝王将相的政治活动转向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正统史料,考古、档案、文物及域外资料都是可资利用的史料。“时间之减”指尽可能删除神话、考证传说,通过确凿的考据重新叙述古代历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不是从“天地剖判”或“混沌初开”说起,也不是从星云凝结和地球形成说起,而是从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开始,以商朝为出发点,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以所知商朝实况为鉴别传说的标准,吸纳殷墟发掘的考古研究成果。
四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学说和阶级概念之利用。张荫麟早已关注到唯物史观,他利用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学说中的部分概念和分析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并使用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路径。
民族危机刺激张荫麟史学研究中民族主义之彰显,而中国近代史学转型中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唯物史观两股思潮也在其史学研究中有所体现。他的历史观和治史路径有创新独到之处,亦有鲜明之时代印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