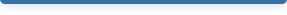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面临复杂多变的环境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正在经历世界性赤字,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其中,自然还有我们自身的教育赤字、医疗赤字、话语赤字等。作为人文学者和文化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总结经验、直面挑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心竭力。
立场、方法与目的
作为体量最大、从业人员最多的学科之一,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自2017年起开始五条腿(即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走路。随着“四个自信”逐渐深入人心,“三大体系”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越来越成为学界共识。其中,自然牵涉我国外国文学界的立场、方法与目的之变。
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终究或主要是为了强健中华文学母体的“拿来”。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高举的旗帜。遗憾的是,这面旗帜正在有意无意地被“世界主义”者们所抛弃。后者罔顾历史,罔顾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大谈所谓的“世界文学”。那么,不知达姆罗什、卡萨诺瓦们眼中的“世界文学”是否包括《红楼梦》和“鲁郭茅”“巴老曹”,是否包括大量发展中国家文学和坚持文学介入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即使文学有其自身规律,但存在只是必然王国,并不等于理想王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提供了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方法论:在承认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必然的同时,仍坚定和义无反顾地批判资本主义。
20世纪被誉为批评的世纪,有关方法熙熙攘攘、纷纷扰扰,令人目眩。从形式主义到新批评、从叙事学到符号学、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女权主义到生态主义、从新历史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存在主义到后人道主义等,或是流散、空间、身体、创伤、记忆、族裔、性别、身份和文化批评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等,可谓五花八门。
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心目中的一些经典作家(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曾受到冷落。与此同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颠覆了我国现代文学历经数十年建构的经典谱系,从而将张爱玲等“自我写作”者们奉为经典。这中间除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逆反,恐怕还有更为深层的根由。举例而言,曾几何时,当我们的一些同行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尖锐批评时,有一些人甚至正兴高采烈地拿着弗洛伊德的理论解构和恶搞屈原。
也正是在这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驱使下,唯文本论大行其道。这种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做法,与源远流长的形式主义不谋而合,或变本加厉地延承和发展了形式主义,作者被“死了”,形形色色的方法凌驾于文学本体之上。对近三四十年的外国文学评论领域的文献稍加检索,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是自说自话和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手道”,或是罔顾中国文学这个母体的人云亦云。盛行一时的学术评价体系推波助澜,正欲使文学批评家成为“纯粹”的工匠。学术以某种标准化生产机制为导向,将批评引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模块化”劳作。我们是否进入了只问出处不讲内容的怪圈?是否让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和煞有介事的言不由衷,或是模块写作、理论套用、为做文章而做文章、为外国文学而外国文学的现象充斥学苑?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是否已形成恶性循环?
可喜的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同行正致力于为我所用的“拿来”。比如,新社会历史批评,以及方兴未艾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和价值叙事学。他们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富有家国情怀、彰显国家意识的研究范式,正在逐渐改变业已坚硬的唯文本论倾向,不仅着力开掘作家作品及其从出的社会历史语境,而且将本国读者及其接受和选择问题纳入批评视域。虽然历史不能还原,但历史的维度永远是文学批评的首要方法。只要将“鲁郭茅”“巴老曹”和张爱玲们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那么谁有资格成为民族脊梁、文学经典,也就不言而喻了。
叙事与策略
在狭义文化方面,我们仍面临茶壶煮饺子问题。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叙事水平,亟待同志努力。特别要注重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主动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文化底蕴、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多年以来,尤其是在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学术史研究、学科史研究和话语体系研究方面迈出了较为坚实的步伐。以《外国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动态研究》为代表,显示出我国外国文学界在方法论上完成了重要转型,社会历史批评和学术史研究、学科史研究向度得到有效彰显。与此同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其十余个语种、国别、区域和类型分会“八仙过海”,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叙事学转型等方面的著述不胜枚举。这关涉我国外国文学的众多从业同行、一批刊物和大量成果。在此,仅就文学伦理学批评和叙事学转型稍加评点。
文学始终离不开伦理,就像其不可能不浸淫于审美传统。正如蔡元培所指出,我国伦理学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历时两千余年。但是,受林林总总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冲击,文学伦理学批评被放逐久矣,直至近十余年在聂珍钊的倡导下形成态势。他的主要观点是,人类文化经历了“自然选择”“伦理选择”,正在或即将经历“科技选择”。这无疑值得重视和讨论。
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叙事学转型,即从形式主义向价值和认知转化。申丹从潜台词出发,探索隐性叙事。傅修延从叙事价值论出发,认为如何在智人的基础上阐释叙事人是叙事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我看来,这非常符合我国的话语体系建构。当西方仍在血缘论向度上纠缠种族民族问题时,中华文化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认识论层面淡化了血缘在族群和社会构成中的作用。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人文化成,也即叙事化成、认知化成。正因如此,当成吉思汗的子孙融入中华文化,也便不再具有侵略性。而满族同胞入主中原后改建的故宫三大殿,也便成了太和殿(天人之和)、中和殿(人人之和)与保和殿(人己之和)。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疑大有可为,也是我国学术界、文化界砥砺奋进的历史使命和现实目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