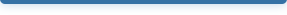长期以来,围绕着国富国穷这一问题的解释,形成了不同版本的决定论。其中,又以制度决定论和技术(产业)决定论两种类型最具代表性。而在进一步的追问中,制度决定论往往会退回到地理、气候、宗教、文化、殖民甚至物种驯化等历史偶然因素的解释中。在技术(产业)决定论中,特定产业或经济活动的选择往往成为解释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尽管技术(产业)决定论者赋予了国家、企业更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对国家为何拥有、如何持续发挥在高质量经济活动中的引导乃至塑造作用,则语焉不详。
无论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技术(产业)决定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国家这一关键行动主体是否具备国家能力,以及国家能力的来源等基础性问题。两者都在“国家应着力于何处”这一问题上陷入了理论叙事的混乱甚至循环之中。制度决定论者往往将某一类型的制度视为唯一答案,而忽视了制度的多样性以及国家内蕴的组织性质和整合能力。技术(产业)决定论则往往忽视了基本政治秩序和国家能力的必要性,而后发工业化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往往需要国家发挥强大的统合、引导和组织能力。
《国家发展的道路》一书立足中国发展的伟大实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制度决定论和技术(产业)决定论,并对国家发展的道路问题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缺乏“中间层次”概念,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更需要从鲜活的实践出发,从相互协同和累积因果的角度,而非单向的线性决定论思维上,丰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解。对于理解国家兴衰这样的宏大命题而言,我们更需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方法论根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框架内,重新审视制度决定论和技术(产业)决定论中的制度、技术的内蕴,获得理解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乃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复杂作用机制的一个新的分析进路。
在引入国家这一主体视角之后,回答国富国穷这一问题时,首先有必要将所解释的时间段限定在一个相对范围内,这是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和“天命论”的关键。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经济发展的内容、结构和动力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财富载体、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上,具有截然不同的范围和性质。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帝国和民族国家之间,在权力的运行方式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三者的关系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将国家穷富分野的因素无限地向前推演,只会使现有解释国家兴衰的理论过于复杂,以至于在留下无穷争议的同时,没有更多值得现代国家和政府借鉴的经验,尤其是那些将决定性答案引向我们无能为力的自然因素或者历史偶然因素的论断。
事实上,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具有以下特征:具有建制性能力,与当时的技术浪潮相适应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国家有能力保障一定的政治秩序,完成对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激励和动员等。但要持续地具备上述特征并非易事。研究表明,在1960年总共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跨入高收入阵营。总体而言,国家发展是一个多因素综合的动态过程,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自我强化的综合系统性作用的结果。第一,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领域的多种因素相互反馈所形成的系统作用,构成了影响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持续决定着国家发展。第二,构成结构因果性的多个因素之间存在协同演化的关系,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但其中存在着最终决定这一结构性因果关系能否保持“不可逆”的因素。失去这一因素,该结构因果关系将不复存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而言,这种确保系统“不可逆”改变的最终条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第三,国家能力对于形成初始发展和维系长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国家主导的发展,并非强调国家的单一作用,而是市场机制、国家干预和社会结构三者契合与协同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化的动力机制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能力的结构、来源和变迁动力,对发展道路有着重要影响。
基于上述观点,制度决定论者的谬误不仅在于将最初变化的原因视为系统最终发生质变的原因,而且认为这种变化只能沿袭“特定类型的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进而决定经济绩效”的线性逻辑。与之相反,技术(产业)决定论者貌似坚持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却将生产力等同于技术乃至产业,而未能结合生产关系的视角,从整体生产方式上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本质。与此同时,技术(产业)决定论者的取向,还容易忽视生产关系适应性变革从而释放和激发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
理解中国发展道路,须聚焦国家能力的独特性,并结合经济活动的选择与发展,系统考察从重工业优先到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推进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传统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桎梏。这一历程不仅是实践层面的创新,更催生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通过提炼中国经验,将国家主体性、制度特征与体制优势融入理论框架,形成兼具历史唯物主义根基与中国特色的分析范式。这种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既源于对“西方中心论”的解构,也体现在对本土实践的理论升华。它拒绝教条化移植,强调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探索制度与技术协同演化的中国路径,最终为全球发展理论注入新的解释维度与实践智慧。